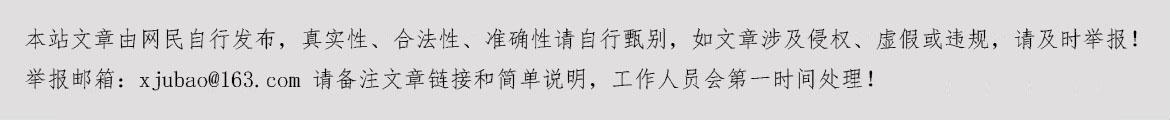“我理解的当代艺术就是真实呈现,是刺破‘他者式假想’的一把利剑。”——嘎德(总策划,日目Remu计划创始人)
大千当代艺术中心“珠穆朗玛的回响”由西藏地球第三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大千当代艺术中心主办,日目计划出品。群展现场呈现了19位西藏当代艺术家的最新创作,在展览中,没有被过度定义的概念,没有抽象而遥远的叙事,没有故弄玄虚的“反符号”争辩,只有作为时代亲历者深刻的看见,臣服于真实生活的思辨,还有具体到细微日常的诉说,带观者短暂的进入了一个立体交织、浪漫质朴的微缩“地方”——真实的西藏。
展览现场
策展从“地方”概念出发,以装置、绘画、影像等多重媒介展现西藏文化的样貌和个体独特的情感,深入走进展厅,能清晰看到作品以逐渐递进的方式,从传统体裁过渡到当代议题。在这其中,嘎嘎21以枯木、金花为载体的装置作品《拉萨河》环绕着整个展厅,观者随着作品的指引穿行于其中,如侧耳乐章般感受着有关生命的起伏和音律。
《拉萨河》,嘎嘎21,木头装置,尺寸可变,2022
“空间、地方、自然”一词来源于华裔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,他在《地方感:人的意义何在?》一文中提出,“在微观意义上的地方不仅是人的避难与呵护场所,还是血缘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纽带。而在宏观意义上的地方是人心灵的栖息地……人作为一个个体,他认识世界,就是从调动各个感官去感知环境开始的。”在策展人之一刘玥拉姆的眼中,作品能够打动她的就是与“地方”的紧密相连中,更具有感知力或源自艺术家自主自发体验的那一部分。
展览现场
刘玥拉姆是出生于内地,毕业于加州艺术学院,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年轻学者,她擅长以喜马拉雅宗教中隐含的哲学命题为母题,以跨学科辩证式思考进行当代艺术实践的挖掘与研究。在本次展览中,网易艺术邀请拉姆共同探讨西藏当代艺术家的生长脉络,发现从“地方性”的角度出发,便能够找到西藏当代艺术的主体性。
《非相18-不空成就佛》,嘎德,丙烯,手工藏纸,藏香原料,高强度泡沫,53X37cm,2020
表达来源于迫切的需求
“你知道吗?在西藏的年轻群体中,大家对潮流文化的热爱甚至比内地要大很多,苏州站有一件作品《世界屋脊的现代化》中拍摄了很多“喇嘛风可乐”,艺术家本人也是一个西藏潮牌的主理人,他们改良的康巴藏装把很多传统的服饰现代化,我觉得这还挺有趣的。”刘玥身着轻便时髦的藏族服饰,戴着一对极简风的金色耳环,在展览现场诠释着关于当今西藏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。
《世界屋脊的现代化》中藏族老僧人正准备喝一罐可口可乐,经验中神秘而严肃的宗教背景交叠生动的普世人性、熟悉的商品标识,让观者不禁感叹,传承与开放、精神性与普世性,因其处于西藏文化语境中才能被呈现的如此淋漓尽致。
《世界屋脊的现代化》,尼珍,摄影,2013
艺术家贡嘎嘉措在系列作品中讨论着资本主义对西藏这“最后一片净土”带来的改变,将当下随处可见,象征着“低级文化”碎片贴纸覆盖在严谨参照度量经比例绘制的佛像全身,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“宗教符号”,打破着西方中心化语境下,以精英阶层为主语定义文化阶级的体系。
HeadLessBuddha©️贡嘎嘉措
社会性的改变通常伴随着个体的对不确定性的恐惧,但从艺术家作品中所构建的交融、和谐、共存的关系,我们也可以窥见西藏本土文化中关于“无常”的智慧,即任由一切体验流经我的身体,外界的一切都为我所用,而我始终稳稳居于生命的中心。正如弗朗西斯·培根提出的,“宇宙正如它本身足够大,大到恰好可以作为人类心灵的栖息地。”
贡嘎嘉措的立意不止于提出问题,作为少数族裔,他给出的答案具有超越二元的价值。贡嘎曾在采访中说道:“有趣的是,资本主义侵蚀了传统的一面,但通过其发展的愿望,促进了文化的另一面。人们可能会争辩说,新的物质主义会使文化不再真实。但现代实践的问题则在于,它对文化的客体化往往是带有剥削性的,使那些产生文化的人处于失败的境地。另一方面,当宗教实践变得过于极端时,它可能也具有压迫性。我的理想是两者能够共存,我试图通过我的作品来反映这一点。”(节选自“贡噶嘉措超越‘潮流’的艺术:以商品为材料,拼贴出时代的真实样貌”)
边巴的一组绘画作品《窗》,三幅中整体使用的灰褐色、窗缝两侧暗红与灰橘的色块、房间里围巾的剪影、正在燃烧着的烛台、映在窗户上或明或暗的空格,每个元素都在搜寻着观者身体里关于家乡和时间的记忆。他通过墨拓记录下这些随着现代化建设逐渐被淘汰的老窗户,再通过自己的感受进行二次创作,呈现着藏地人民在迎接新时代变化的阵痛中,最本质动人的情感。边巴不希望西藏在经济形态的不断发展中成为留守的“最后一片净土”,他说:“我只是对曾经的生活有一点恋恋不舍。”艺术提供着这样一个空间,让人在现实与情感交错中,抛开利益与评判,纯粹的表达与获得慰藉。
《窗》,边巴,布面综合,2013
黄威是毕业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汉族艺术家,多年来进行西藏主题的创作与实践,通过点染(唐卡绘画展现颜色渐变的一种方式)的手法,一点一点勾画出他首次见到“日晕”后的圆通意蕴。而蓝色,是他抬头所望见的,西藏天空最澄澈的颜色。
《圆通》,黄威,纸本设色,200x200m,2021
策展人刘玥负责此次展览作品的选择,她说“西藏的艺术家对生活中细致末节的变化都有很深的感触,我觉得这是最打动我的一点。西藏老一辈的都是职业艺术艺术家,但现在很多是公务员,他们不是职业艺术家,他们关注时代的迭代和更新,白天上班,晚上回家画画,艺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需求,一个想要诉说自己的出口。”
《背着翅膀的人》(局部),诺次,布面丙烯,120X120cm,2021
无论在西藏的诗歌、艺术、歌曲中,还是在信仰、仪式里,“地方”这一概念都持续在人们行为的互动中彼此构建。人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均质、空洞的空间里,反而,生活空间、周遭环境恰恰因为所有人奇思妙想的流动而充满浪漫,趣意盎然,周遭的空间也不再是冷漠的容器。
借本次“珠穆朗玛的回想——空间、地方、自然”展览,网易艺术邀请日目计划一起深入探讨西藏当代艺术背后的文化土壤。
日目计划联合发起人刘玥拉姆
Q:本次策展逻辑选择了“地方依恋”,在你看来青年艺术家如何解构本土文化?
A:青年艺术家,比如说本次展出的《普布次仁》纪录片的导演旦增色珍,她一直都在拍摄拉萨本地真实的小人物,通过记录人物在时间长河中的流变去看见这个地方的变迁,她觉得诉说的必要。地方依恋对每个艺术家都很重要。
《珠穆朗玛峰神女》,余友心,布面重彩,2006,120x90cm
Q:在西藏当下的文化语境中,艺术家们日常会关注和思考哪些主题?
A:我发现他们永远对一种“患得患失”的情绪有很深的体悟,简而言就是他们语境中的无常,对于“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”的思考。这也是他们能够坦然接受生死这种大概念的一个基本原因,他可以非常坦然的面对很多大的事情。这种无常,在很多别的包括日本文化里面肯定也有,但西藏人的无常是基于他们一套非常缜密的信仰观念。
《情器世间》,西热坚参,藏纸、油画、蜡笔,81x78cm,1991
Q:在观看西藏现当代艺术时,不可避免会看到浓厚的文化信仰和艺术家个人自我意识同时存在,作为策展人你怎么看待传统与当代的关系?
A:对,关于这个问题艺术家们会思考很多,就是符号性的表述是不是有必要的。其实外界有一部分对西藏当代艺术的直接观念是,你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逃出符号的表达?今天的你还在画佛吗?你怎么还不进步?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。